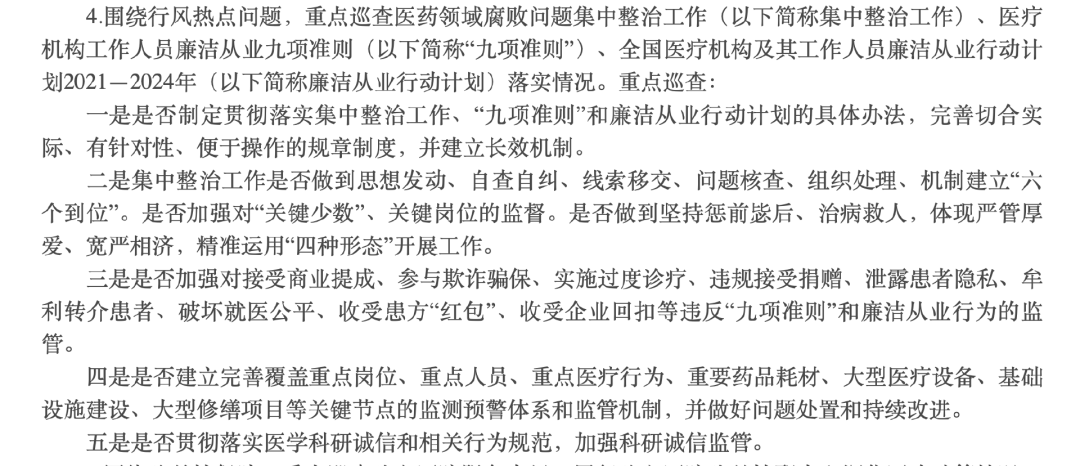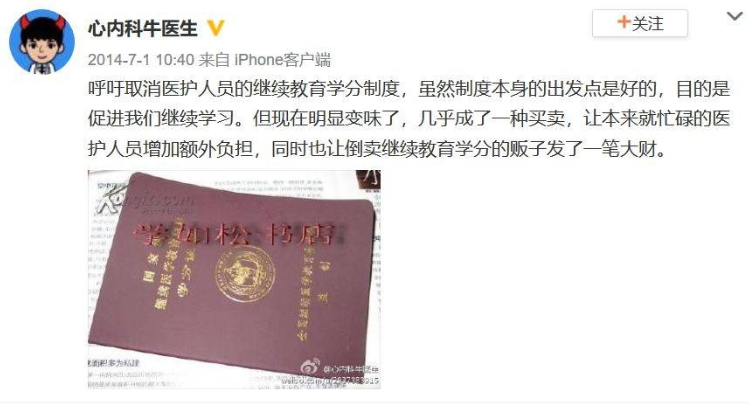医学生亲述: 疫情之后,如何为医
- 作者: 徐艳
- 来源:财健道
- 发布时间:2021-11-13 13:46
医学生亲述: 疫情之后,如何为医
【概要描述】在这段“成为医生”的旅程中,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国际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掀起了波澜。波涛汹涌间,舆论场上纷纷扬扬:医学网课闹剧不断,实习困难重重,鲜花与掌声的背后是医护人员数不尽的苦楚,医学生们同时经历着心灵洗礼与自我拷问。笃定或动摇,放弃或坚持,医学生们将会做出怎样选择?
- 作者: 徐艳
- 来源:财健道
- 发布时间:2021-11-13 13:46

过去的五年,医护行业似乎进入了至暗时刻,层出不穷的“伤医、杀医”事件让医护人员笼罩在密云之下。在2016-2020年公开报道的139起伤医事件中,共有180位医护人员受到伤害,其中16名医生离开了人世。
在这段“成为医生”的旅程中,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国际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掀起了波澜。波涛汹涌间,舆论场上纷纷扬扬:医学网课闹剧不断,实习困难重重,鲜花与掌声的背后是医护人员数不尽的苦楚,医学生们同时经历着心灵洗礼与自我拷问。笃定或动摇,放弃或坚持,医学生们将会做出怎样选择?
01
学医的成本有多高?
但胡羽的学医之路才刚刚开始。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至少需要5年本科和3年的住院医生规培;想成为层级更高的主治医师,需要硕博学历、行医经验以及持续不断的科研成果产出。特别在公立医院体系,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选拔制度,某三甲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曾讲道:一个优势科室内,至少有10员大将专业技术过硬,但除了现任主任、候任主任、1位明星医生外,剩下的7人可能一生都怀才不遇。
尽管前路漫漫,当被问及“毕业后会不会选择做医生?”时,她斩钉截铁地回复道:“当然,不当医生这五年不就白读了吗!”疫情期间医护人员的英雄事迹会让她热血沸腾,但学习的重担却又压得她喘不过气,但“自己选的路哭着也要走完。”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曾在采访中提到:“我光读医就用了13年,而一般人上大学读四年之后就上班赚钱了,而我比别人多出来的9年时间,基本都在读书,拿很低微的学生工资。”

正如张文宏所言,大部分本科生在参加规培期间基本工资低,尽管有国家下发的生活补贴,但也只是杯水车薪,社交网站上常可以看到刚毕业的医学生吐槽收入微薄。在上海的科研硕士规培第一年,每月薪资扣除房租水电仅有千余元;在地级市三甲医院工作的骨外科硕士,半年试用期内每个月薪资到手仅2千元……而同期进入互联网大厂、或者金融行业的校友已拿上了数万的月薪。
事实上,单从成本角度来看,在中国就读医学院的成本远低于美国,根据U.S. News公布的医学院排名,73所公立学校中,2018-19学年的州内平均学费约3.5万美元;外州的平均学费则接近6万美元。因为在美国医生是高薪职业,申请竞争激烈,学校提供的奖学金很少,不少医学生毕业后会背负医学教育债务。
然而对于更多中国医学生而言,“高薪”不会总在明面上提起;在“成为医生”的道路上,很多人似乎选择了“用爱发电”。
02
余白也秉持着相似的想法,他的父亲是广西的骨科医生,一手传统接骨术在省内赫赫有名。不过伴随现代技术的发展,传统的接骨技法逐步被先进的手术所取代,余白最初选择学医是希望继承父亲的衣钵,除此以外,他就想做一名普通的小医生,“如果家人、朋友身体不舒服,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帮他们一把。”
然而疫情让他跳开了个体思维的小圈子,当他看到84岁高龄钟南山院士主动请缨,连夜前往武汉对疫情进行初步诊断调查时,他顿生感慨:“小时候以为钟南山是一座山,长大了才知道他真的是一座山。”
在国内TOP级医学院就读的小宇也拷问过自己:“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会选择去吗?”他给自己的回答是:“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职业,那救死扶伤就是你的责任。如果有牺牲和奉献,能够从病毒手下抢一个人,就值了。”这股热情充满着感染力,弥漫在小宇所在的新生群体中,似乎经过了疫情,小宇身边的朋友更坚定了学医这条道路。
03
乱花渐欲迷人眼
除临床医学外,疫情期间备受关注的“疾控”,令公共卫生专业成为单位争抢的香饽饽。一位北大医学部公卫大五学生告诉「财健道」,去年以来,各省卫健系统开始“抢人”,房子在内的各类福利补贴“都端了出来 ”。4月底,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成立,高层对疾控的重视预示着公卫将成为新的显学。
疫情也在高林的学习生涯中打下烙印,“社会压力、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一步一步逼着我去走上这条路,疫情作为助推器,坚定了我的选择。”在他的眼中,医生是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能够帮助他“混口饭吃”,在吃饱饭的背景下,也能帮助别人,这就是他朴实的心愿。
高林深知以科研水平为标准的现行医生评价体系中,医生不仅只有“救死扶伤”这一项工作,大部分医生同时担任着研究员的角色。白天值班,晚上整理资料、做科研是家常便饭。“如果不是当下这个残酷的社会环境,我又怎么会选择这样一份辛苦的工作呢。”作为过来人,在面对学弟学妹学医的热情时,高林总是额外谨慎。2019年高林曾回到母校进行宣讲,面对学弟学妹们如潮水般热情的询问,高林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他站在讲台上,一口气向学弟学妹们介绍了医学生在大学里需要学习的53本课本。
“学医”的过程是漫长的;成为了医生,高强度的工作还在继续,需要面对医患矛盾、医疗纠纷等问题,或许还要接受人生哲学的拷问——理想和面包的抉择。对于尚且热爱医学的人而言,这终会是一场身心煎熬的修行,如果换作对学医不算坚定的人,痛苦可能会放大百余倍。
“但凡是有些动摇的,我都不会推他一把。学习是一回事,感动是另一回事。”阿力与高林有着类似的观点,他也希望后来人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相比之下,小宇更为警惕。
“不敢说学医是一件很崇高的事,但我觉得人的生命是非常崇高的。”小宇对专业选择的谨慎来自于对生命的尊敬,他认为医生是要面对人的生命的,在做选择前需要问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把握去对待你面前的生命。“一厢情愿是风险很高的的一件事。”
04
“我感觉这并不像前景一片光明。”阿力自诩不是校园里的“卷王”,但也被迫跟着同学的脚步做出学业规划。他不能理解,在姨夫成为医生的年代,当时的本科学历相当于现在的医学博士,但是伴随着人才的涌入,为何现在的本科学历就像是一张废纸,而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或许博士只是成为医生的一块敲门砖。
阿力抱怨着医生愈来愈严重的学历内卷,认为自己深受其害,他感觉自己处在漩涡的中心。南京某一本院校护理学专业的井妍与阿力有着相似的感受,虽然并没有直观地从本校毕业生的就业数据感知到这一点,但她也隐约地察觉到这股压力。
井妍的猜想并非空穴来风,去年3月28日,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扩招的通知,预计当年研究生扩招18.9万,专升本扩招32.2万,而扩招的方向集中于临床医学、公共医学、人工智能等领域。长期来看,一线医护储备人才厚度增加;短期来看,在就业岗位锐减的疫情期间,延缓之策亦刻不容缓。
“尽管未来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但这也意味着更多优秀的人选择加入医生队伍为社会做贡献。”阿力想,竞争总是残酷的毕竟在一个班级里总有第一名和最后一名,但如果这换来的是整个社会的持续性进步,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
在这个推崇速度和效率的“速食年代”,这份需要“潜心”的长征之旅更显困难重重,但正如《小王子》里描述的那样:“你在你的玫瑰花身上耗费的时间,使得你的玫瑰花变得如此重要。”经过了试金石的磨练,“医生”这个字眼在医学生们笃定的信念和高昂的成本下更为厚重,在后疫情时代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亦欣
免责声明:本网注重分享,并不意味着赞同本文观点或证实内容的真实性,请仅做参考。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在此向原作者表示感谢。除非无法确认,本网都会注明作者及来源。如有版权异义请及时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