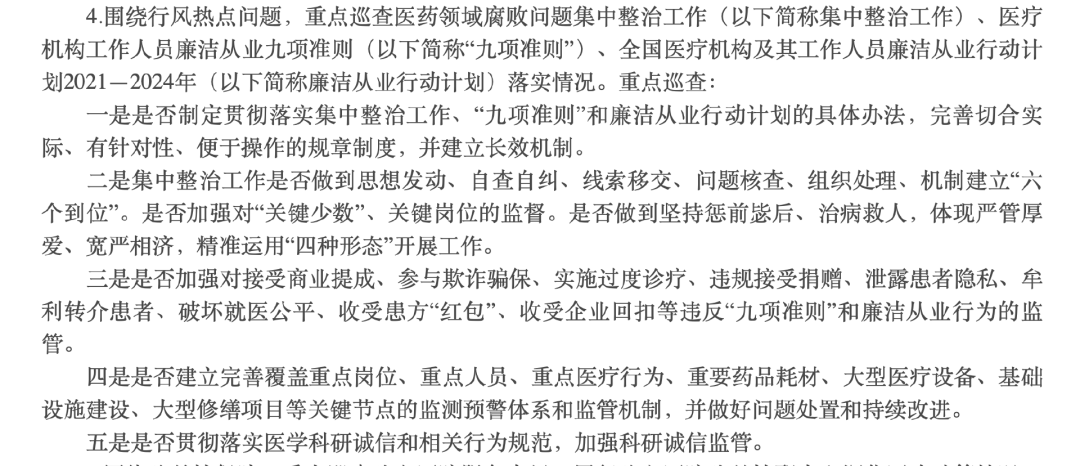当我们谈论涉及13亿人的全民医保时,到底在谈论什么?
- 作者:
- 来源:
- 发布时间:2020-10-02 10:10
当我们谈论涉及13亿人的全民医保时,到底在谈论什么?
【概要描述】医疗领域有一个不可能三角:不管在哪个国家,医疗服务的低价、高质、便利,三者无法共存。
中国在上个世纪六十年到八十年代的医疗保障体系中,牺牲了质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这个世纪初,上一代保障体系瓦解,新的医疗保障体系尚未建立,10多亿人在病有所医这件事上,度过了痛苦的二十年。
- 作者:
- 来源:
- 发布时间:2020-10-02 10:10
医疗领域有一个不可能三角:不管在哪个国家,医疗服务的低价、高质、便利,三者无法共存。
中国在上个世纪六十年到八十年代的医疗保障体系中,牺牲了质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这个世纪初,上一代保障体系瓦解,新的医疗保障体系尚未建立,10多亿人在病有所医这件事上,度过了痛苦的二十年。
2003年-2011年,建成全民医保,在医疗服务低价、高质、便利的不可能三角中,在每个点中都做出部分妥协,达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2011年至今,原本达成的平衡被打破了,当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和全民医保的保障范围不匹配时,中国的医改又一次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价格、质量、便利性,在这个医疗的不可能三角中,这一次,我们到底要作何取舍?
2006年10月,当全民免费医疗的倡导者、北京大学海归学者李玲教授进入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进行了一次讲课后,人们普遍猜测,新医改道路之争的天平开始倾斜,政府主导、补贴公立医院、提供免费或者部分免费的基本医疗服务的路线,将主导本轮医改。
一年后,风云突变,在对外征集的9套医改方案中,市场派提出的全民医保路线开始占据压倒性优势。
在那次决定了13亿国民未来就医命运的道路之争中,全民医保,而非全民免费医疗,成为一种更为现实的选择, 但公众对于全民免费医疗的渴望从来没有停止过。
在医疗服务这种关乎人类基本权利的的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全民”+“免费”天然就具有对社会大众的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在医改路线之争落定、全民医保铺开后的十几年中,每逢医疗领域内有冲突发生,无论是医患之间的剧烈冲突,还是新药的定价问题,政府主导的“全民免费医疗”都会作为一切矛盾的终极解决方案,被重新提及,引起热议。
全民免费医疗,作为一副寄托了对现实医疗状况不满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图景 ,随时撩拨着公众脆弱的神经。
在一项事关13亿国民福祉的路线选择上,持续性的争论自有其必要性。但造成困扰的是,这些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个中国医疗体制改革和医保制度的设计和实施。
20年裸奔史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估报告 ,宣告过去20年中国的医改“总体上是不成功的”。
这是官方极为罕见的一次公开承认的改革失败,10多亿人在病有所医这件事上,度过了痛苦的二十年。
除了“排队两小时,看病五分钟”、“全国人民看病上协和”的痛苦体验外,医疗价格大幅增长:从1980年到2003年间,居民到医院的平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增加了66倍和171倍。
与之相对应的是,上一代的全国性的医疗保障制度几近崩溃——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合作医疗解体、城市劳保医疗无以为继,仅有极少数人能享受公费医疗。
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4。
新的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在2003年,拥有基本医疗保障的国民也不过1亿出头——当年的城镇职工医保只覆盖了1.08亿人。
沉默的大多数,在面对飞速上涨的医疗费用时,近乎裸奔。根据第三次全国性的卫生服务调查的结果,2003 年底,64.5%的居民在寻求医疗服务时必须完全依靠自费。
对于贫困阶层而言,连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都享受不到,“小病拖,大病扛,重病等得见阎王”是他们那20年间的真实写照。
就在跨入新世纪的第五年,四川农民付利松,身患癌症无钱医治,绝望中,支走了6岁的儿子,点燃炸药自杀身亡。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一份官方层面公开承认改革失败的报告为导火索,新一轮的医改拉开了序幕。
医疗问题,作为转型时期矛盾最为尖锐、最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面之广,牵涉利益之多,难逢对手。
医院、药企、医疗器械公司作为医疗服务及其相关产品的供给方(简称供方),想要得到高昂的回报。
病人作为医疗服务和产品的消费方(简称需方),希望得到廉价甚至是免费的高质量医疗服务和服务。
建立一套覆盖大部分国民的保障机制,弥合供需双方的预期落差,即能让供方得到合理的报酬以激励其提供质量可靠的医疗服务,又能让需方在家庭支出不会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可负担的范围内,看得起病看的好病,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功课。

过去20年里,国人关于就医的痛苦记忆的根源之一,正是全民性的医疗保障体系的缺失——上一代医疗保障体系的土崩瓦解之时,新一代的保障体系尚未确立。
新医改的操刀者国家发改委史无前例地向外界征集了8套不同的医改方案,来设计中国未来的医疗保障制度。参与者从国务院下属的研究机构,到顶尖学府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再到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麦肯锡等智库和咨询公司不一而足。
这8套方案,在“医疗到底应该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扶持公立医院还是民营医院”,“钱是投给医院,还是通过保险直接补贴给患者”等种种细节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究其本质,这8套方案是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的两条实现路线之争:
一种是政府主导派倡导的全民免费医疗路线——政府投钱给供方,也就是公立医院,公众可以免费或者部分免费享受基本医疗服务;
另一种是市场派主张的全民医疗保险路线——政府的钱投向需方,建立一个覆盖大多数人的医疗保险,通过第三方保险向医院付费购买基本医疗服务。
医疗的不可能三角
怎样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覆盖大部分国民的医疗保障制度 ,全球其实都没有太成功的模式。
欧元之父蒙代尔提到过一个“不可能三角”: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自由流动,三者不可能同时存在。
一部名不见经传的美国电影《diner》,非常聪明地化用了这个理论,电影的主角拥有一个餐厅,他为自己的餐厅做了一个醒目的标语“我们的食物又快又好又便宜”,但在这行醒目的宣传语底下,有一行小字写到“以上只能选择两种”。
医疗领域也有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不可能三角。
过去全球10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管在哪个国家,医疗服务的低价、高质、便利,三者无法共存。
免费,其实是一个被误解多年的概念。医生提供技术和服务,药企提供药品,医疗器械公司提供设备,不可能是一项慈善事业,免费提供给病人,一定有买单方。
所谓免费医疗原名公费医疗,筹资来源是税收——归根到底,也是要全体国民买单的;而全民医疗保险是专门的医保缴费,筹资来源是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共同承担。在这个意义上,全民公费医疗和全民医疗保险的差别并不大。
全民医疗保险模式和全民免费医疗模式,都是通向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路径选择,全球大部分国家根据各自资源禀赋在二者中择其一。
迄今为止,没有一个国家,建成了完美的低价高质便利的医疗保障制度,只能在成本、质量和便利性三个要素中寻找一个平衡。
美国的医疗服务水平高,但是以高价而闻名全球——占据了全美17%的GDP的投入。
英国被广为称颂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成本适中——卫生支出占GDP的10%左右,质量不错,但是等待时间太长——若非急症,经常要等上一年半载。
奥巴马的医疗政策顾问、美国乔治大学法学院教授格里格·布洛赫在一次关于中国医改的圆桌会上建议,“牺牲不可避免,关键看政策目标是什么”。
几十年前,中国建立的医疗保障制度,牺牲的是质量。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通过财政出资的公费医疗;城市的企业职工通过企业出资的劳保医疗,农民通过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合作医疗,分别在定点医院、农村医疗站就医。

虽然是一种形式上的全民免费医疗体系,但质量不高——大部分农村地区的人只能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应付少数传染病,对大病慢性病几乎无计可施;浪费极大—— 劳保医疗和公费医疗体系下一人生病全家吃药和倒卖医保药品等现象猖獗。
在中国,公费医疗这个词早年间是特权阶层所拥有的医疗保障制度,所以在中国有些盛名狼藉,于是在后来的路线之争中,更倾向于使用全民免费医疗一词。
免费二字一出,盛行一时,拥趸者众。
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正是由于看起来很美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无以为继,才导致上一代全国性的医疗保障体系的瓦解。
到九十年代时,农村合作医疗解体,劳保医疗无以为继,仅上海纺织行业拖欠职工医疗费就达上亿元,有地方欠费白条要几十年才能还清。
实际上,以1994年的两江试点为起点,到1998年国务院的44号文《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为标志,中国就已经开始探索通过社会医疗保险建立医疗保障体系的道路。
但由于整个社会对于医疗的投入并不高——从1978年到2005年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仅仅是从3.02%增加到4.73%,而且这些费用的增加,主要是个人和社会支出的增加,而非国家公共财政。
所以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在这些年里进展缓慢,1998年到2005年的7年间,城镇职工医保覆盖了1.38亿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了1.79亿人,另外有近10亿人仍然处于裸奔状态。
到底是沿着此前既定的全民医疗保险路径加以完善,还是重新开启全民免费医疗之路?要重新开启全民免费医疗之路,必然要公共财政增加天量的投入——此前那种低投入的全民免费医疗之路已经被证明破产了。
虽然江湖之下的全民免费医疗的呼声极大,但庙堂之上的人要考虑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事实上,就在全民免费医疗还是全民医疗保险争论的后期,卫生部的两位高级官员,时任部长高强,副部长黄洁夫都在不同场合直接表态,中国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因为“全民免费医疗是一笔非常大的支出”。
所以在2008年公布的新医改的最终方案中,全民医保派看起来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各级政府将在三年内投入8500亿,其中三分之二将被用于补需方——也就是投入全民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力求在2011年,全民医保能够覆盖90%以上的国民。

医院的黄金十年
从2003年建立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中国就已经实质走上了全民医保之路。
1998年建立的城镇职工医保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保险,雇员和雇主共同缴费参保;针对从农民的新农合和后来建立的城乡居民医保(针对城市老人、学生和无业人员)都遵循了自愿原则,以财政投入的方式,政府承担缴费的大头,个人交很少的一部分。
只是苦于政府投入和当时经济发展水平所限,不但覆盖人数有限,以当年新农合人均筹资30元的标准,能提供的保障极其有限——初期农民每次住院的平均报销金额只有690元。
借助新医改的东风——原计划在三年内投入8500亿,到收关的第三年,实质投入超过了12000亿,全民医保网络迅速建成,从2003年覆盖仅仅1亿出头的人口,到2011年底时覆盖了全国90%以上的人口,兑现了新医改的承诺。
不仅仅是财政的投入,中国的优势在于,对于已确立的路线,从上到下,从政府到企业,从国家到个人的全社会总动员。
新医改全民医保路线的所带来的杠杆效应,撬动了整个社会资源医疗领域的倾斜。
恰逢中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十年,1998年起步的全民医保体系,在中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覆盖了全国90%以上的人口,医保基金的收入也分别从2003年的千亿出头跳涨至2013年的10700亿,这也是本轮医改最值得称道的战绩。
中国的医疗市场上,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支付方正在形成,但比医保基金增长更快的是医疗费用的支出。
中国2003年到2013年,是全民医保的极速扩张期,也大型公立医院的黄金十年,医院的每年的收入增幅超过20%。
由于医疗专业知识的瀚如烟海,医院不仅对患者具有压倒性的信息优势,甚至对监管者也是如此。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的医保部门作为市场上主要的支付方,都和医院进行过控费的拉锯战,不夸张的说,各国医保和医院的博弈,就是一部宫斗史。
在中国,在此前市场派提出的全民医保路线中,除了增加投入尽快覆盖全体国民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一套与之相称的供方市场——一个去行政化的、充分竞争的供方市场,各种不同所有制的医疗机构通过竞争降低医疗服务价格。
虽然市场派赢得了需方改革的胜利——全民医保路线的确立;但政府派赢得了供方改革的胜利——公立医院地位的进一步强化。
所以,在中国的医疗市场上,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的组合:
市场化的需求方——通过医疗保险购买,而不是行政指令分配医疗服务;
行政化和垄断化的供给方——公立医院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民营医院完全无法挑战公立医院,形成一个充分竞争的供给市场。
在这样一个结构失衡的医疗市场上,由于公立医院垄断了供方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医院,而不是医保基金强势主导了医保资金的流向。
“聪明”的医院早就心领神会了“虹吸”医保资金的法宝——搭乘现代医疗科技的快车,升级医疗行为,使每个病种的消费单值提高。
现象上来看,就是微创手术普及化、检查检验手段升级、更多的耗材、更好的设备、更贵的药品,因为治病救人的名义被运用于临床,而未仔细论证每个行为是否值得。
从官方到各研究机构披露的数据看,中国的医疗浪费惊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医疗保险司司长陈金甫在2018年的《财经》年会上披露,在中国目前的医疗消费中,30%是过度医疗。
虽然到2011年,绝大部分的人都有全民医保兜底,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已经从2000年前后的6成降低至2013年的3成,但是个人的卫生支出绝对值,实际上并没有降低:从 2003年的3678亿跳涨至2013年的10927亿,涨幅近300%,大大超过了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
所以这十年来,中国的医疗市场上呈现出一幅奇异的图景:
一边是,迅速建成的全民医保体系和飞速增长的医保基金;另一边是,跳涨的医疗费用和一座座营收几十亿床位几千张的超级医院的落成。
《无尽的硝烟:医改十五年拉锯战》一文中提到,在中国,10年前,收入超过10个亿就可以称为超大医院了,现在年收入没有50亿,院长参加全国论坛都难上主席台。
结果是,夹在中间的患者,怨言依旧。全民医保建成所带来的获得感,并没有完全转化为公众的满意度——在2013年第五次医疗服务调查中, 仍然有36%的住院患者认为住院花费过高。
但无论如何,在全民医保跌跌撞撞的十年中,本轮医改达成了它的两大政策目标——保基本,广覆盖:也就是在适度增加医疗投入(医疗服务价格不能上涨太快)的情况下,为13亿国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服务。
三角平衡被打破了
在前十年间,在医疗服务低价、高质、易得的不可能三角中,中国的医疗保障制度试图在每个点中都做出部分妥协,达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适度增加而不是无限增加医疗投入,在可负担的价格范围内和可接受的等待时间里,保障大部分国民得到基本的、而不是全部的医疗服务。
但是由于医保基金在前十年中的粗放式发展,也由于医疗技术的进步和老龄化,这个微妙的平衡很快就被打破了——医保基金就快要跟不上医疗费用的上涨的脚步了。
所以到了2011年,中国的全民基本医保体系建成的年份——经由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确认,已经覆盖了中国13亿人口,同时也是各地的医保基金开始显现危机的年份。
虽然在老龄化的背景下,各国的医保巨额亏空是一种常态。但像中国的医保体系一样,在运行短短十几年后,就出现巨大的赤字风险,实属罕见。
后来因三明医改闻名全国的老工业城市三明,城镇职工医保的亏空早2011年就高达2个亿,城镇职工医保的统筹账户上不但拿不出钱了,还欠了当地22家公立医院一大笔医药费。这个亏损的额度,占全市当年财政收入近15%。对一个老工业城市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兜底的巨大窟窿。
一千公里以外的,也是重工业起家的徐州,也走向了医保改革的十字路口。2011年,徐州的职工医保统筹基金亏损7个亿,比三明的窟窿大得多。
就在第二年,连经济发展强省如广东,也开始出现了危险的苗头;城镇保险统筹基金的收入增幅开始低于支出增幅。如果按照这种态势发展,不加以制止,基金没钱是迟早的事。
远不止广东,黑龙江省等多地都陷入了医保统筹基金可能要没钱的焦灼中。
到2013年的时候,全国有225个统筹地区的城镇职工医保基金收不抵支,占据全国统筹区的32%之多,其中22个统筹地区,已经将历年来所有的医保结余资金全数用光。
当时的一份报告预测,2017年开始始,城镇职工医保基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显现,到2024年的时候,基金会出现7353亿的严重赤字。
医保资金穿底,听起来似乎只是一个庙堂之上的人需要考虑的抽象问题;但实际上,却是一个13亿人要真切面临的就医困境。
2016年,因为医保超支,没有和医保部门就医保资金的拨付达成共识,位于长沙的湘雅第二人民医院就公开表示,“长沙市医保,除危重病人外,只能提供门诊就医,暂不能办理入院就医”,拒收了一批医保患者。
不仅仅是长沙湘雅二院,不到年底,各大医院的医保额度基本上都被花光了,更有医院,医保资金的额度只够用大半年而已。
于是,每到年底,各大医院“推诿患者”、“拒收患者”的报道屡见不鲜。
在医保资金压力最大的那几年,甚至有医生半开玩笑告诫病人,如果要做手术,建议选在上半年,因为下半年医保吃紧,不一定能做上手术。
在博弈中,患者的就医需求未被充分满足,医患矛盾频发。医院把责任归结为’医保额度不够’,推给医保支付方,医保支付方也因‘总额预付’的简单粗放而备受诟病。
毫不夸张的说,对于一个承担了整个社会卫生总费用近三分之一的医保基金,它的穿底危机,是一把悬在整个中国医疗界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三明模式和超级医保局
旧平衡被打破之后,中国需要在医疗的不可能三角——价格、质量和便利性上做一个新的调整。
就在此时,后来因有效降低了畸高的药价而闻名全国的三明模式闯入了政策制定者的视线。
中国式全民医保的特色是,统筹层次低,一般是由地市级甚至县级政府,负责当地医保资金的筹措和支出。更通俗一点说,是各地管各地的,北京的医保缺钱了,绝不可能管上海要。
以三明这个曾依靠厂矿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城市为例,2005年到2011年之间,人口不升反降,年轻人流失到外地,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改变,缴纳医疗保险的人变少了,需要用到医保基金的退休人员变多了。
詹积富从福建省药品监督局调回家乡三明市,担任副市长之时,正是当地医保捅了窟窿的2011年。
早年在家乡与药品行业打交道了5年,深谙这个医保中的支出大头有诸多灰色地带和水分——三明医保的钱,60%通过医院支付给了药品,养活了一大批医药代表,也养肥了一批医生和有医保职能的相关方。差不多同一时期,三明先后有8名公立医院院长被查出有药品腐败问题。
詹积富回到三明做的第一件事,此前没有人做过;就是把这些分散在各部门的医保职能拿出来,单独组建一个机构,专门管医保。
此前,各地人社部门管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卫生部门管新农合,过于分散的医保机构和统筹级别太低无法形成强大的制约力和议价能力。
詹积富以强力手腕,让分散在三明各处的24个医保经办机构在一年后被整合到一起,成立了三明医保局。医保基金从财政部门手中转入医保局,从此,与医保相关的制度设计、操作实践全由三明医保局做主,政出一家。
一个地区性的医保超级支付方形成了。接下来,以医保为杠杆,打破了药品的省级统一招标,市级有资格开始议价,解决近二十年医改中的痼疾,将久降不得的药价中的水分挤出。

这一政策实施仅一年,三明全市的药费在两年内从9亿直接下降到5.67亿,下降幅度高达37%,职工医保统筹基金立刻止住了穿底的势头,在2012年也就是第二年结余了2632万元。
虽然三明模式尚存争议——除了控制药价外,还控制了异地就医和部分高价药入医保,但对于全民医保这个全球性的难题而言,哪里有完美的模式呢,它对于正在承受巨大赤字压力的医保系统而言,不啻于久旱逢甘霖。
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来三明考察过后,三明模式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开,就连几年后成立的国家医保局都部分借鉴了三明的模式。
在国务院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中,国家医疗保障局问世:人社部、卫健委和民政部的职工医保、居民医保、生育保险和医疗救助资金集中统一管理;将此前分散在发改委、人社部和卫健委的医保药品定价权、医保药品目录调整、采购、签约定点医疗机构等职能也都集中在这里。
国家医保局成立后,各地也陆续建立地方性医保局,试图打破权力分散的问题,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超级支付方的格局。
这是全民医保走到现在的必经之路,人们急需一个强大的医保支付方,和药企谈判降药价,抗衡医院对医保的无节制食用过度浪费。
这个从本质上带着诸多民意和期待的超级支付方,除了通过大幅度打击欺诈骗保,用追回的数亿医保资金向民众展示其维护基金安全的强大决心外,还背负着政府迫切解决重要民生问题的“使命”。
国家医疗保障局,而非医疗保险局,从称谓上就能看出这个超级支付方所承载的期望。保险,更像是一种手段和实现路径;而保障,意味着承诺。
医保是药神吗?
就在超级医保局成立的那年夏天,上映了一部极尽煽情的电影——我不是药神。
任是铁石心肠的人,看到一贫如洗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初为人父的青年男子,跳钢管舞的单亲母亲在黑暗中哭泣:「我病了三年,四万块钱一瓶的正版药,房子吃没了,家人也被我吃垮了」,「我不想死,我想活着」,「有病没有药是天灾,有药买不起是人祸」,都会鞠一把同情泪。

这是一个有关现代社会的伦理困境和道德隐喻的故事:由于现代医学的进步,几乎需要等死的白血病病人,只需要定期服用一种叫格列卫药物就能得救,但这种救命的药物,价格之高,高到普通人倾家荡产也难以承受。
对开发新药的药企而言,药企没有足够的利润激励,就不会从事新药开发这件极具风险的事,技术进步停滞,未来我们没有新药可吃;
对于病人而言,有救命的药,但因为没钱吃不到,只能等死,有违现代社会的伦理;
医保作为中国医疗市场上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支付方,似乎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因为击中了无数人的内心,这片电影的票房高达30亿。
汹涌的民意淹没了一切,几天后,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到刚成立的国家医保局调研,提出“加快推进抗癌药降价”,第二天,医保局就开了相关会议,抗癌药谈判被提上日程。最后,18种抗癌药谈成了17种,包括多种靶向药物,平均降幅50%以上。
故事似乎有了一个光明的结尾。
但对于中国的医保体系而言,远不是结束。
以格列卫为代表的高价创新药,正是当下各国医保体系的困境的一个缩影。
如果说来自供方的浪费是一种有可能通过技术被解决的困境——实际上,自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已经在试图通过支付方式改革来控制过度医疗,但其实医保之困更在于老龄化、疾病谱系的变化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带来的医疗费用的增长。
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范围内,新技术和新药陆续被研发以及推进上市,高昂的药价几乎成了所有创新药的代名词,价格高到会让普通人倾家荡产的地步。让这些高价的创新药进医保,不但是药企和病人们的共识,也是政府惠民工程的一部分。
高价药纳入医保,成为各地医保局顺意民意的一种常规操作。虽然高价药众多,但是医保基金有限,能被入的药就意味着是有限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哪个群体的呼声越高,医保局则回应得越快。
因为自2011年医保覆盖了95%的国民后,全民医保的口号无处不在,在一个商业保险文化孱弱的土壤里,全民医保是多数国民面对疾病时的唯一一道防线。
在中国人拥有全民医保的这些年,医保承担了支付以外的更多功能:解决社会问题、民生问题,甚至上升为政治问题,用来评价一个地方政府对民众的承诺是否足够有诚意。
在中国,现在应如何定义医保?
如果看两组数据,第一组是,这十年来,中国的医保筹资水平只有GDP2%左右,而保障范围96%以上国民六成以上的医疗费用。第二组是,2018年已有106个统筹区的职工医保和183个统筹区的居民医保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缺口金额分别为83.4亿和154亿元。
这意味着,中国正在用的低水平的筹资水平满足更多人的医疗需求。
无论三明模式和国家医保局如何辗转腾挪,都逃不开这2%的限制。
2005年发轫的那场新医改为全民医保所奠定的政策目标“保基本”,这个没有具体内涵和边界的原则, 一直是各部门内部争论的焦点,在国家医保局成立2年后,再次被提起。
“保基本”引申出来最直接的问题是,什么是基本?作为供方的公立医疗机构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医疗服务?用什么药?
而各地各部门占的角度和立场也颇不一样。人社局的观点是,从经济学角度出发,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卫健委的观点是,从医学上给它一个范畴,什么是小病,什么是大病,用一刀切的但问题是,给庞大的疾病划一个免费的疾病范畴,
上个世纪,急性传染病是国民健康的致命的威胁;如今,每年几百万新增的癌症,成为了常见病,如果抗生素可以被囊括在保基本的范围内,那么层出不穷的癌症的新药是不是基本?罕见病只能用高价孤儿药,没有替代药物,不吃就活不下去,这是不是保基本?
今年夏天,一种罕见病的特效药70万一针要不要进医保又引起了热议。
争论无果,但所有医保职能部门都承认一个事实:保多少的根本还是由收上来的医保筹资款多少决定的。
如果在当下,目前保基本的范围和公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不再匹配, 原定的政策目标保基本还能继续吗?随着疾病谱系和技术的的变化,如果想要获得更高的保障水平,我们还能提高医保的缴费水平吗?提高多少才够用呢?
2019年,中国的年人均收入刚刚跨过1万美元的线,我们所能看到的医疗技术、治疗水平、可选择的治疗方法和人均收入是我们3-4倍的发达国家是一样。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接近1万美元,英国比较节约,人均4000美元,以中国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水平,如果希望获得相当的待遇,我们可能需要拿出相当于收入的40%用于医疗支出。

医保部门自医保基金发生穿底危机以后,曾经两次试图提高医保的筹资水平:
第一次发生在2016年,原财政部长楼继伟在《求是》上撰文透露,正在研究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的政策——按照原来的政策,只有在职员工需要缴纳医保。但引起公众不满,甚至被批评“会丧失民心”,后来便不了了之。
第二次发生在上个月,城镇职工医保在设立之初,公司缴费的大头放在统筹账户,个人缴费的全部和30%公司的缴费放在个人账户,可用于医疗用途的支出。这个为了适应当时特定时代背景的筹资机制,在多年后也埋下了隐患。个人账户像是一个鸡肋,越来越贬值,相反职工医保的统筹基金的保险能力并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国家医保局想要进行一场改革,将个人缴纳的部分划入个人账户不变,而单位缴费全部纳入统筹基金,也就是说,原本划入个人账户的 30% 部分,将改变去向。
但这个被学界一致认可的政策,却引起了舆论极大的反弹,民众的不解、困惑甚至是反对铺天盖地而来。
职工医保的筹资的提升尚且困难重重,针对收入水平更低人群的城乡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想要提高缴费水平,似乎更是一个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问题是,当公众对于全民医保的期待和筹资水平发生冲突时,中国的医改又一次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价格、质量、便利性,在这个医疗的不可能三角中,这一次,我们到底要作何取舍?
前任卫生部长陈竺在离任前曾经被问到,“医改是不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位在任上主导了新医改的前任部长摇头说不是, “因为战争总有结束的一天。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原镇江市医保局局长、1994年“两江医改”的主要参与者林枫对本文的指导
(吴靖 徐卓君 八点健闻)
责任编辑:文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