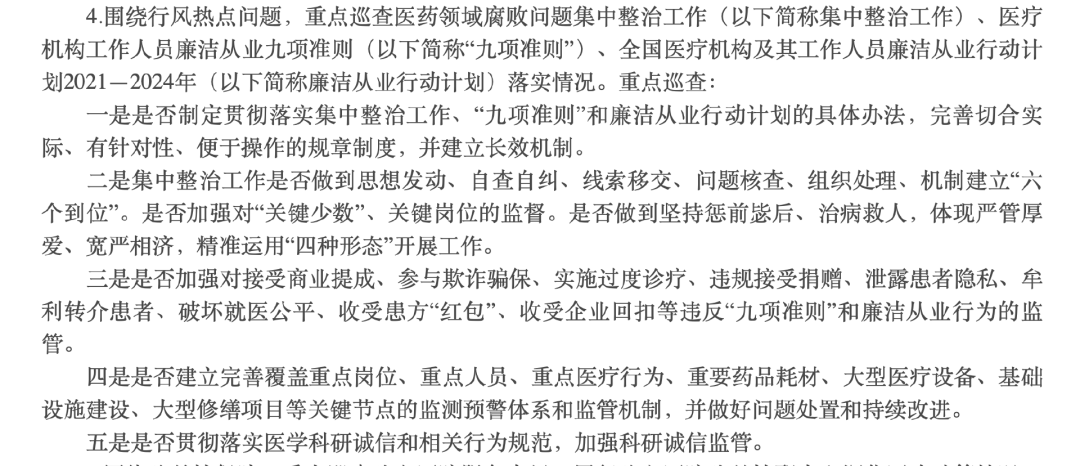1921年初秋,洛克菲勒二世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下称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登上远洋轮渡“亚洲快线”。在长达一个月的漫长旅途中,陪伴他们的,是一大箱专门讲亚洲和东亚的书籍。
他们专程为一家中国医院而来。这一年的9月16日,也就是100年前的今天,壁立千仞的协和医院将在北京举行开幕典礼。在1915年以来的6年筹建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协和投入了千万美元级别的资金。
典礼上名流云集,除了中国总统府、内政部与教育部等政府代表,还有世界各国一流大学校长及科学家、国际卫生组织代表。与开幕会并行的,是一场空前的学术交流盛会,上述重量级嘉宾参与了在协和为期一周的深度研讨、演讲交流、临床展示,为中国学术科研、社会教育带来了新鲜血液。
▲ 开幕典礼期间,协和董事会成员在医学院的走廊合影(手持礼帽者为洛克菲勒二世)
能举办如此体量的科学盛会,在当时中国,其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协和落成前的70年间,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跌入历史谷底,现代医学基础几乎为零,救亡图存之路举步维艰。
向西方学习,成为不少仁人志士的理念,但同时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还是负笈渡洋的留学生,如胡适与鲁迅,都在与西方文明碰撞、体验阵痛、试图交融。
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之后,通过商业文明支持中国现代化的慈善机构随之而来——中国现代医学“东齐鲁、西华西、南湘雅、北协和”,全部为那一时期的外资慈善机构捐赠。其中,这所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创办的北京协和医院,自那时起就一直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最高峰。
洛克菲勒一世创办的美孚石油公司,一度垄断了全美的炼油工业和油管生意。即使在远东,其仓储码头也能在黄浦江岸绵延超6英里。在成为巨富之后,19世纪末,他开始将更多精力转向慈善,并深刻影响了百年之后的比尔·盖茨。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正式注册成立,对那时的它来说“整个世界都是广阔的试验场”,而首要的,它将目光投向了积贫积弱、站在历史拐点上的中国。
因为洛克菲勒二世的坚持,协和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位教授和每一位学生,都对标全球顶级标准。1917年,协和医学院招生;1919年,同时开始招收女生;1921年,协和医院投入运营。和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院校一体的模式相同,协和医学院与协和医院也被打造成为密不可分,且教学科研与临床三位一体的尖端系统。
百年之后,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以“精英中的精英”概括之,概因“考虑到民众的利益和人类的终极利益,这个终极利益就是健康和生命,因此容不得这批人素质不高,容不得这批人不够聪明、不够智慧,容不得这批人品德不够高尚”。
协和对现代中国的意义,远不只在当时。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德先生和赛先生于风云激荡中传入中国。千年帝制已成历史,古老的东方亟待一场现代化的疾风骤雨。作为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医学开始在华夏大地落地生根,与之相伴的,还有协和百年传承的医学精神。
在远东建立现代教育支点,不可能一蹴而就。协和项目并非顷刻决定,一开始,洛克菲勒基金会只是对中国教育有种模糊的构想。因此,为保证科学性与效率,1909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出了第一批考察团。考察地包括日本、印度、朝鲜、中国,历时6个月后,带回整整六卷本关于东亚地区教育、医疗、体制等各方面的报告。
然而,考察得越细腻,基金会就发现阻力越大,想象中的“芝加哥大学在中国”计划难以实现,考察团铩羽而归。
此次蓝图几乎被推翻后,异国文明陌生甚至刻奇的社会样本,让决策团队看到了文明生态的不同。西方文明在18、19世纪异军突起的原因,在于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勃兴,想要让传统而古老的中国短时间内完全吸纳现代文明,显然是异想天开。
不过这次失败并非在中国慈善项目的终点,反倒是真正的起点。基于上述调查,洛氏基金会先是于1914年召开了为期两天的“中国会议”, 继而,又派出协和项目的第二批考察团。成行前,考察团受到美国总统威尔逊接见,并携带上了由基金会、美国国务卿威廉·布莱恩及中华民国驻华盛顿公使夏偕复联合签署的介绍信。抵达中国后,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携副总统黎元洪也接见了考察团。
考察团分两次,于1914-1915年,历时8个月之久,对中国244所医院中的88所进行考察,著成共10章节中国现代早期医学发展的珍贵史料:《中国的医学》。
据此,洛克菲勒基金会集合美国教育界、科学界与基金会通力研讨的结果为:西方的医学科学和外科手术,可以作为普世文明的“礼物”送给中国。
“礼物”一经落地,便奠定了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基础,并为其注入了科学与人文结合的内涵。
《时代周刊》将协和称为“东方的约翰·霍普金斯”,而后者则是能与哈佛医学院比肩的存在。新冠疫情开始后,国人惊讶地发现,美国的疫情数据统计并不由卫生部发布,而是由权威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来担纲。
这所医学院是在19世纪末迅速崛起的,它源自19世纪德国柏林洪堡的大学学术体系——自由、科学、开放——被媒体评为“这一千年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前文提到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就曾去德国留学。1893年以前,美国大学没有现代医学实验室,也没有真正的医学研究者。他一边感叹美国医学科学之落后,一边坚定了改革美国医学教育,甚至整个国家医学理想的信念:医学活动应该脱离简单商业行为,上升至科学与人道主义的范畴。
那一年(1893年),韦尔奇将德国划时代的大学制度引入美国医学教育,自此,美国现代医学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出现了以“约翰·霍普金斯四巨人”韦尔奇、霍尔斯特德、奥斯勒、凯利为首的一批医学新星,也哺育了全国甚至世界的现代医疗教育。
1897年,洛克菲勒一世开始进行慈善捐赠,他和韦尔奇都已经看到教育和现代医学的慈善价值,并对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基金会的影响力充满动力。
彼时,鸦片战争以来的封建中国,正被西方世界视为“东亚病夫”。1900年以前,寥寥可数的中国医院几乎都是教会医院,其体系与能力,完全无法与教学科研与临床一体的约翰·霍普金斯相提并论。20世纪初,中国人办的西医诊所几乎不向老百姓开放,社会大众包括不少知识分子,都很难接受西医的“开刀”疗法。
于是,中国急迫的现代化需求与洛氏放眼全球的慈善事业理念不期而遇,在医学科学的生命线碰撞出一束火花。如果说,积贫积弱的中国是张求知若渴的白纸,那么,看到远东地区慈善教育价值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便是一位科学而专注的教师。
这时,洛氏内部冒出来一位关键人物——弗雷德里克·盖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顾问。
一方面,盖茨对世界范围尤其是在中国的慈善事业抱有很大兴趣;另一方面,他本身就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
韦尔奇回到美国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建实验室、办医学预科、确立住院医师制度,最大限度让临床、科研、教学相结合,以理想主义指导科学精神,成就了美国医学教育体系上的壮举。在那里的求学经历对盖茨造成了巨大影响,也让他对推行这一现代医学方案抱有十足的热情与信心。
在联合了医学、教育、资本、政治等各界人士之后,盖茨力倡基金会据报告《中国的医学》在中国兴办现代医学。报告指出,应首先以最高标准建立一所媲美约翰·霍普金斯的中国本土医院/医学院,首选地点为北京、以英文教学为主,并做好长期工作的准备。
理想主义必然价格不菲。报告指出,想让一所“约翰·霍普金斯”在中国拔地而起,造价将是难以估量的巨大数值。
历史便总逢曲折处独木生花——在战乱和殖民倾轧的残酷年代,巨额资金并未成为阻碍协和项目的绊脚石——巨额跨国捐赠,虽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内部引起争议甚至质疑,但最后还是获得了坚定支持,1913—192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协和项目陆续投资达1000万美元。
这为协和创造了科学、自由、政治友好的开放环境,使其可能媲美国际顶尖标准,最理想化地实施建造项目。
协和医院坐落在王府井与东单之间,即清朝豫王府旧址之上。医院建筑负责人柯立芝初到北京,甫一落地,他便为中国古宫殿的雄美姿魄所震撼,当即决意推翻此前设计,改筑一所中西合璧的校园与医院群。
医院外部顶部中国古典宫殿式造型,雕梁画栋、琉璃瓦楞,下接西式洋楼,内部取用最高级的医疗科研设备。其中,包括水汀管、门锁,甚至每个房间的抽水马桶,都是从美国进口而来。经4年营造,最终建成包括55栋楼宇的建筑群。
这用于基建和初创的1000万美元,只是洛氏捐赠协和项目的开端。
设施环境不是终点,协和医院的目标,是打造世界顶级医学院,科学精神与人道主义精神的结合,要求所有成果必然也必须服务于活生生的人。
所以,协和招揽人才时不拘一格,向世界顶尖看齐。无论黄皮肤或白皮肤,无论用中文还是说英语,更无所谓寒门贵胄之分,只要足够优秀、也必须足够优秀,就能成为协和一员。
只要成为协和一员,基金会就为其准备最高级的待遇。教授们一年有5千美元薪水与住房津贴,对应0.2美元/斤鸡蛋、0.3美元/斤牛肉的物价,生活水平不输美国中产阶层。
建立之初负责教学的老师,大多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重量级专家,比如协和第一任外科主任邰乐尔(Adrian S. Taylor)就是“美国现代外科之父”威廉·霍尔斯特德的得意门生。当时,协和药理系还曾试图招聘哈佛医学院的药理系主任克莱耶,但因哈佛学生太喜欢他而抗议,最终没能让他成行。这足见当时协和的吸引力,也说明,初期协和在本土人才方面亟待规培,多数系科还是由非中国人主持。
名师云集、全英教学,让协和一开始便能与全球最先进的医术与科学无缝接轨。例如,曾名动天下的吴阶平医生,就是协和医学院最后一批全英文博士研究生。
好的师资环境,也需优质生源配合。对于标准极高的医学院来说,学生不仅要学习医学知识,还需具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英语方面的基本功。刚开始招生时,中国本土综合性大学的生源质量不达标,协和只能自办预科班,严进严出的高标准下规模效益严重不足。
于是,洛氏基金会不仅负责协和医院的运营,还决定每年固定为中国的13所综合性大学提供资金。在洛氏持续资助综合性大学8年之后,协和才得以停止自办预科,从综合性大学招收学生。
全方位的捐助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有句俗话讲,“救急不救贫”,基金会在战争时期对协和医院的捐助已获卓著成绩,功成身退是必然。1947年,洛氏基金会展开了终止与协和财务关系的讨论会议。
洛克菲勒二世突然出席了那次会议。他早已不是基金会董事成员,放手洛克菲勒多年。但在那次会议上,洛克菲勒二世却用心良苦,巧妙地说服基金会在结束之际,最后捐献1000万美元作为协和医院项目的收官之笔。
1000万美元几乎占到194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全年预算的一半,如果捐赠成功,那么,洛氏对协和医院的捐助总额就达到4500万美元。1947年,在内战中的中国,美元与法币的汇率一路飙升,从1:12000涨到了1:73000。
这使得协和医院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历史上对外“最大的单笔礼物”。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对共同创建和经营协和的那一代人来说,这项跨越民族和历史的事业背后,闪耀着科学的理想主义精神。
医学无国界。当慈善家、外籍教授、医学研究者、医务工作者,在慈善无功利旗帜下汇聚一堂时,他们的心态便突破了简单的一时一地、一国一族,成为不被民粹主义和政治功利主义裹挟的存在。
无论他们后来拥抱何种身份,“协和人”的烙印都永远成为他们医学生命的勋章。医学与教育,本就具有普世一致性。
1937年,卢沟桥事变,协和医院曾对美国员工表示,应听从美国务院建议,在条件尚能允许的时候,尽可能早地离开中国,然而最终,没有一个人离开。
2021年9月10日,协和医学院“可胜大楼”揭牌,以纪念林可胜这位协和百年史中的巨擘。饶毅曾撰文,称其为中国生命科学之父。
林可胜,美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华医学会会长,是中国最早获得国际承认的科学家之一。1897年,林可胜生于新加坡华裔望族,其父林文庆曾为厦门大学校长,姨父是永载全球医学史册的伍连德——1910年,他扑灭了哈尔滨鼠疫,1915年当选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亦曾参与协和创建。
在获得爱丁堡大学博士学位并在芝加哥大学进修后,1925年秋,林可胜来到了协和,生理科客座教授兼系主任,两年后转为教授。
在后世的实验记录中,有一段林可胜痛苦扭动的影片被传颂至今。那时,他是为研究阿司匹林的镇痛作用,把缓激肽注入自己的动脉血管,使身体产生剧烈的疼痛,再用阿司匹林来镇痛。这种“以身试法”的实验并不仅此一项,后来著名的组织胺刺激胃分泌的实验,他也在自己身上做过。
1925年,林可胜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并任主编。杂志创办后,他对每篇论文都认真审查,亲手一再修改,直到完全满意才同意公开发表。很快,刊物便获得国际生理学界的认同,成为中国当时少数几个具有国际水平的科学刊物之一。
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协和生理系一直是全球范围内举足轻重的学术高塔。
如此成就,来自林可胜一丝不苟的,忘我甚至到有些极端的医学科研精神。据载,因为在协和做实验往往从早到晚,所以他常派人到东来顺买来大饼、酱牛肉和咸菜,与团队边吃边工作。虽然家很近且条件也很好,但他总能说服夫人,让自己留在实验室和大家一起啃大饼。
拥有顶尖能力的他为人倒是风趣幽默,授课时还有一项绝活——熟稔绘画的他能用双手在黑板上同时画图,在学生中获得了高于外籍教授的赞誉。据说,他最早引起未来妻子注意,就是因为他画了她的像。
当然,协和不止有林可胜。创立起的28年内,协和在风雨飘摇的中国培养出了数不胜数的大师,如内科张孝骞、李总恩,外科曾宪九、吴英恺,妇产科林巧稚,儿科绪福棠等。
时任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是中国妇产科历史上最耀眼的明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林巧稚便在女性盆腔病症、新生儿溶血症以及妇科肿瘤研究方面作出了前无古人的开创性贡献。
上世纪40年代末,她开始了对滋养细胞肿瘤和其他妇科肿瘤的研究。因为,据她掌握的不完全统计,每年大约有100多万妇女死于癌症,这使她深感癌症是妇科疾病的最大难点。
所以,她带领学生对葡萄胎、子宫绒毛膜上皮癌进行长期跟踪检查,总结了1948年7月到1958年12月底接收158例人滋养细胞肿瘤病例,发现良性葡萄胎大概率转移事实,推翻了外国医学界认为良性葡萄胎不转移的结论。
从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协和还在短短10年之间完成了现代医学的属地化进程——骨干大部分都由中国人担纲,并能做到向外输出人才:协和第一任解剖系主人考德里回美国后任教华盛顿大学和圣路易斯大学系主任,外科、生物系、寄生虫系教授回美均担任各大学校医学院的系主任及教授。
这得益与协和完备的设施与师资环境,更得益于一以贯之精英教学模式。协和医院教学与临床实习要求之严苛,可以说是达到令人“闻风丧胆”的程度。
首先是入学难。预科期间,学校规定医学生必须读完中文、英文各192小时,生物384小时,数学96小时,化学544小时,物理384小时并保证兼备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关知识。然后才能获得协和医院的入门考试资格,经教师推荐、特殊面试,最终决定能否顺利被录取。
其中,面试之特殊还在于,老师会请考生来家吃饭,全方位探讨家庭、生活、社会问题,并一律使用英语对答。
总之,学生是宁缺毋滥,且顺利考上之后,还有恐怖的淘汰制度。老协和曾有一种说法——一门挂科要补考,两门挂科要留级,三门挂科直接扫地出门——并且,协和的及格线并非及格的60,而是优秀与否的75。
1919年考入预科班的21名成员,到1927年时只毕业了4名,还有6名同年毕业的则是插班和降级生。
吴阶平曾回忆过自己在协和的一场口试。那时,他的一年级生理学教授正是林可胜,期末考试中口试时间为15分钟,但因师生二人的水准都远超寻常,“林教授的问题接二连三,越问兴致越高”。
考了近一小时后,秘书请林可胜去参加某追悼会。吴阶平才感如获大赦,却听林教授紧接着吩咐,“你等着,我很快就回来”。等回来,又问了半个小时,才算真正结束考试。
考完走出协和东门的路上,吴阶平只感疲惫不堪、天昏地暗。但也就是教授不放过的科学精神与格外“亲切”的关照,将吴阶平带上了生理学的研究道路。在他入校以前的十年中,只有吴阶平主动在二年级继续选修了生理学课程。
实际上,当时与他参加考试的其他7名同学,能力也并不差。能在协和苛刻的学制里存活的,都是“尖子”。但在协和,只要能看到更好的可能性,就没有人愿意停留原地。
后来,吴阶平在1959年设计的利用回盲肠进行膀胱扩大术领先全球,直到70年代甚至80年代,这一技术才通过欧美书籍和杂志,作为最新手术方法传入西方。
如此竞争压力中,协和医院那时诞生了一种脸色,叫“协和脸”——尽管医院餐食住宿质量极高,健身房、杂志阅览室每日开放,周末还办舞会和踏青活动常常。但大多数人都因压力问题食欲欠佳,为了读书研究躲开休闲活动,最终炼就一张苍白的“协和脸”。
但先苦后甜的成果,确实是傲视群雄的斐然。英文授课、西医体系、外国教师——这些后来颇受质疑的模式,对当时的协和人来说都不成为问题。因为,在医学技术、科研方面,协和足够自信。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1941年,协和医院的骨干医生吴英恺被派往华盛顿大学进修。吴英恺加入前,其导师从未做成过食管癌切除手术,经手病例无一存活。但此前,吴英恺与协和医院同事共同完成的11例同类手术中,有6例病人长期生存,他后来将成功经验介绍给了导师。
1948年,他又赴芝加哥大学进修。后来,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导师曾对吴英恺说,“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是从你们(协和)那里学来的”。
这是因为,除了向西方世界寻求先进资源,当时的协和在办学与行医方面,有自己的眼光。物色教授时,不只聘请技术领先的外国教授,还希望能够找到“受过很好的中文传统教育,同时兼有现代观点”的中国人。
协和,不仅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捐赠出来的协和,更是中国的协和。
寻聘教授的阶段,有人为协和医院推荐了胡适。作为医生,胡适不是一个合格的选项,但在文化和现代性眼光上,他是却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所以胡适随未加入教授团队,但却被选入协和医院董事会,代表北大参与合作了后来的一系列办院事务决策。
这种自发的民族精神与全球视角,让协和成为点亮中国现代医学的明灯。
当然,协和医院的一流水准并不止于名师名医,更在与它走向大众、走向基础卫生医疗体系建设的扛鼎之举。
成立之初,协和就设置了社会服务部,保证医院和广大病人间的联系。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曾任协和社会服务部主任的张中堂回忆道,在协和医院,社工人员的地位与医生平起平坐,每月工资75元,每年能休假4周。
在他撰写的《话说老协和——社会服务部二十年》的文章中,张中堂描述了自己为病人尹仲安排装假肢的过程:
请技师查看,确定可以装假肢。但经了解,费用最低为70元,病人因患慢性化脓性骨髓炎已在协和住过12次院,病人是单亲家庭,实在无力支付。
于是,社工首先咨询患者母亲的雇主,说通雇主支付其中35元,又申请社会服务部拨款结清另一半。最终在当年6月21日为病人安上假肢、给病人一副拐,并用1元2角钱给他买了一双鞋。
有协和医学生表示,进校前,他以为医生便是为有钱人开诊所、开药方来牟利,但在协和学习几年过后,他愈发相信,“医药并不是超越社会的职业,而是社会事业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在上世纪20到30年代,陈志潜,也把现代医学的前沿硕果,带向了广大人民群众。
1932年的春天,中国曾爆发过一场席卷全境的霍乱瘟疫。那次疫情传播达4个月以上,遍布全国超60个县及地区至13万人死亡,死亡率达30%。
陈忠实在《白鹿原》第25章中写到过这种“两头放花”的恶疾。文中,白鹿村最东头和西头的两家人,分别用独轮推车把“两头或一头放花”的患者推向冷先生的中医堂。那里已被同样的独轮推车挤了个满满当当。不久后,这些独轮车就成了病号们的停尸板,“所有村庄的所有庙宇都跳跃着香蜡纸裱的火焰和满地飘动的纸灰”。
就在人们求医无门,纷纷开始寻鬼神问药时,有一个县,却罕见地在那次疫情中屹立不倒,零星的几例,也都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这个县,是河北省定县,其罕见的防疫成效就来自陈志潜。1929年陈志潜于协和医学院毕业,他希望将“一盎司的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的卫生理念更多地带向农村,于是便来到定县农村,开展实地考察。
 ▲ 老协和的公共卫生和卫生学系职员
▲ 老协和的公共卫生和卫生学系职员
很快,他构想出的一套针对中国农村的公共卫生防治方案,能够以每人每年仅0.1美元的低廉成本,建立起覆盖40万村民的农民保健网。
陈志潜接受的顶尖精英教育,让他极明白科学行动要建立在对现实的科学认知上。所以,防治方案去繁就简,先对十来位年轻村民,进行“照葫芦画瓢”的培训,再根据观察,配备使用频率最高、使用方法最简单的医疗药品,让学员们“不求甚解”地实行,最大限度地安抚村民情绪。
最简化的培训方式、成本3美元的便携保健箱和最接地气的村民宣传模式,将定县卫生防疫水准从古代提高到了现代。这是西方科学与农村定习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过程。农民们不被硬性要求“改造认知”,而是先从卫生防治中获益,这就让卫生防治工作水到渠成。
这个“定县模式”,大大影响了后来中国农村三级保健网与“赤脚医生”体系,同时,也扩散到世界各地。
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在《阿拉木图宣言》中提到的“全面的初级卫生保健”,基本是对“定县模式”的复刻。1981年,陈志潜在菲律宾当地考察时发现,当地卫生站药箱里的红药水、阿司匹林、甘汞片正是50年前他为定县存保健箱设置的基础药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北平。时任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林可胜投笔从戎,毅然奔赴抗日的最前线。他将孩子安顿到新加坡后,只身返回武汉,组建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开启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二段旅程,并最终创立了中国的军医体系。
随着战事的发展,林可胜在贵州图云关创设救护总站,培养人才,接受药品和医疗器械捐赠。凭借其出色的学术功底、极强的号召力和组织领导才能,林可胜汇集了荣独山、容启荣、张先林、周寿恺、汪凯熙等协和毕业生,其规模之大、人才之多,远超国内任何一所医学院。
同时,这一救护总站还获得了国际进步团体、个人以及爱国华侨的广泛支持。保卫中国联盟领导人宋庆龄派与中国共产党渊源极深的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与林可胜保持联系并做对外宣传,募集到大量捐款与药品,仅美国的捐赠,就超过6600万美元。华侨领袖陈嘉庚对林可胜“努力之精神”极为赞许,主动逐月由南侨总会捐助一万元给救护总站。
1938年长沙会战之后,大批伤病员涌向后方,很多官兵患有皮肤病,苦不堪言。移驻湖南祁阳的林可胜,便把大汽油桶改装成锅炉,设为简易灭虱治疥站,其疗效显著,因而深受官兵欢迎。
1940年夏,林可胜深入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许多地区不通公路,只能全靠步行。43岁的他光着上身,头包白布,行走乡间70余天。回到贵阳后,“水与污染物管制计划”即刻推出,水致传染病与肠胃病状况大为缓解,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和陈志潜一样,林可胜深知公共卫生的重要性,所以坚持训练部队改善村庄驻地的环境卫生。他的远见是——战后大批士兵复员返乡,星火燎原,便可把农村的卫生搞好。
1942—1944年,林可胜随中国远征军到缅甸战斗,任中缅印战区医药总监,时常每日工作16个小时,身心交瘁。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多次嘉奖他,英美政府,亦多次授勋给他。
如此风骨并非特例,而是协和人的根本所在。1941年12月8日,上午8点,一队日本兵包围了整个医院,禁止所有人出入,并闯入校长住宅拘留了校长胡恒德。
门诊不再开张,病房没有新病人,一个月后医学院全体停课、学生离校。所有设备和建筑由日军改为军医及相关血清研究所用。校长胡恒德及其三位在协和工作的美国人,自此被关押4年,直至日军投降。
时任北京协和医院高级护校校长的聂毓禅并未放弃护校,她尽己所能,安排愿意留下的那一届护校学生都在其他综合大学完成学业、拿到毕业证书。接着,又带领护校成员穿越到大后方,在成都“白手起家”,兴办了临时护校。因为极度贫穷,学生们连纸都没有,却仍坚持学习,后来几乎所有人学会了当地方言。
费孝通回忆,在西南联大时期,内地知识分子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和国家的未来,有着相当纯粹的信心与抱负,展现出的“一往情深,何等可爱”。
一个世纪以来,光芒万丈的协和精神,通过千千万万有名或者无名的林可胜们,普照着华夏大地。其医学与人文主义结合的独特精神,最终是为服务人类事业而存在。
所以,上文中提到过令人“闻风丧胆”教学制度,并不是反人性的“内卷”,而是科学与人文主义融合后的高标准制度体系。
协和非常明白,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严酷的竞争制度,也不能要求所有人以医学事业为毕生追求。学生、教授,与协和医院之间的关系,在残酷淘汰与严进严出的同时,还保留着人性化的双向选择。
比如,入学标准有例外。1921年夏天,20岁的鼓浪屿人林巧稚报考了只招收25名学生的上海场医预科笔试。考到最后一门英语,有位女生突然晕倒,林巧稚不假思索地放下笔,跑去急救,最终没有答完试卷。她以为自己必然落榜,不料,一个月后竟收到了协和医院的录取通知书。
接着,上完3年预科班后,学生可以权衡是否继续进入协和学习,如不想继续,可以回到综合性大学再读一年,获取学士学位。入学一年后,也仍有一次抉择机会,供学生们自由选择去留。
教授地位也并非是仅凭学历与技术判定。抗战初期,林巧稚医生曾被挖苦,一位一门心思搞研究的妇产科主任说,“你以为拉拉病人的手,给病人擦擦汗,就能当教授吗”?下一年,协和便并未续聘那位主任,而选择了林巧稚做妇产科主任。
后来,林巧稚在妇产医学领域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对她来说,救活一个产妇、孕妇,就是救活了两个人。为感谢她的救命之恩,许多在林巧稚手里接产出生的孩子,都被起名为“念林”、“爱林”、“敬林”、“仰林”。直到生命的最后,这位终身未婚的“万婴之母”还在呓语中断续喊道,“快!快!拿产钳来!产钳……”
曾在协和工作的内科医生张之南,回忆过自己在协和的临床实习经历。
当时,他刚成为临床实习大夫,开始跟着主治大夫巡诊。一日,走到一位肝硬变病人床前时,病人突然剧烈呕血,张之南下意识就闪向一旁,但主治大夫却面无异色、上前俯身擦拭。
紫红色血渍浸得白大褂上到处都是。这一幕给了张之南以莫大震撼,让他明白,“主治大夫虽然弄脏了白大褂,但他的心灵是干净的”。
等到他自己也做主治医生的时候,某次巡诊也发生了同样的一幕。他毫不犹豫上前用痰盂接呕吐物、拿毛巾为病人擦嘴。那之后,张之南的实习大夫告诉他:这对他们来说是无比珍贵的一课。
临床、科研与教学一体的制度,并不是简单将医院与学校糅合起来,而是要医学生在知识学习、临床学习、科研工作中成为一个“整全的人”。
当今所谓医德医道,要求医生以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的口号,似乎正在成为某种不可企及的想象。但在当时,“病人为中心、向病人学习”,却是协和医院最朴素而永恒的铁律。
1953年,协和医学院停止招生。因为自协和创办开始,舆论中便一直存在对其亲美、精英主义的质疑,到“文革”时期,这种质疑扩大成为批判和否定。
当时,内科圣手张孝骞曾被派往医院门诊看病,但他一出现,门诊的秩序就完全乱套,其桌前会挤满赶不走的病人。造反派们不理解这个该被打倒的“反动权威”为何有如此影响力,便停了张孝骞的门诊,派他去扫厕所。
没想到,病人就一路跟到了厕所去,不少人追在后面为张孝骞不平,说张主任、你有什么问题,我们给你伸冤去!——只不过,大夫本人也答不出自己的问题出在哪。
就在张孝骞扫厕所的同时,林巧稚也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分配到绒癌病房做护工。已经白发苍苍的林巧稚,在病房里缓慢但细致地洗便盆、倒痰盂,心无杂念,还不时想法子悄悄寄钱给停职停薪的细菌学家谢少文,用英文附注道,“这不是钱,这是友谊”。
经历如此波折,张孝骞等人并未气馁。他们在1976年成功推动协和医大复校方案。1979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协和复校,并列入重点大学行列。
198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时隔33年后重返协和,拨款140万美元以支持协和建设。
现在,被我们奉为大师、神医的人物,对那时的协和来说是理所应当。这些协和骨干们在进入21世纪后,已成为珍贵的“老头老太”,但上述精神仍长存于这些“老协和”人的身上。因为医学是科学,而科学的方向感最终来自于人。
对于老一辈协和人来说,不重视病人的社会服务,就不能被称之为一流。因为任何和一种疾病,都是生理、心理、情感与社会综合影响的结果。医生要治的,是人而非病;医学要医的,不只是人,还有社会。
然而,老协和们追求建立科学与人文主义相融合教育体系,培养全方位人才的理想,却无法始终如一地被贯彻到底。大学医学专门科系与各类专科医院的兴起,是现代医学发展中的必经之路。这也让协和曾经的教学制度、科研体系与临床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2018年初,王辰院士出任协和医学院院校长,上任伊始,他就改8年学制为“4+4”,希望系统能接收培养多学科者从医,“纳天下贤才而选之”。
相比于8年制教学模式,4+4模式的专业课学习时间从5年半缩短至4年,而工、理、文史哲等科目则被广泛纳入协和的教学管道,在大学专业化、医院专科化的分化社会趋势中,反而试图向老协和科研与临床一体的全科模式靠近,希望能在今时今日,设法重探当年的协和能量。
2021年春,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与中日友好医院原副院长姚树坤合作编写的《临床思维》出版,进一步给出了临床与理论相结合的实践范本。在北京协和医院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们能看到,仍有人在不断怀念、反思、学习“协和精神”。
2021年9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协和医院考察时表示,协和为我国现代医学和医学教育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成功救治了大量病患特别是疑难重症患者,“协和医院正是有你们这样的医学名家一代代传承发展,才赢得了今天这么高的业界地位和良好口碑”。
到现在,医学界仍还流传着那句老话:病人与死亡之间,隔着一个协和。
(作者为《财经》研究员,实习生张羽岐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亦欣
免责声明:本文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在此向原作者表示感谢。除非无法确认,本网都会注明作者及来源。如有侵权请及时告知。





 ▲ 老协和的公共卫生和卫生学系职员
▲ 老协和的公共卫生和卫生学系职员